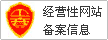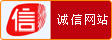哲学是智慧的母亲。世上需要哲学和哲学家。
我总觉得哲学是比较诡秘高深的,就是一门让自己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学问。但有拆字先生说:世界上的事儿,都是曲曲折折的,用嘴说出来,就是哲学嘛。
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,自然不识字,当然更不懂得什么深奥的哲学。但母亲经常说的一些老话儿,现在咂摸咂摸,如陈年老酒,纯美、醇香,感到有哲学道理。
她说她只知道,说话要讲道理,做事要顺天理,为人要懂情理。
话中有“理”,理中带“哲”,母亲俨然就是个哲学家。
我们兄弟三个刚够到桌面高,母亲便规定“吃要有吃相,坐要有坐相”。吃饭,手得端着碗,还要粒粒进口;坐凳,两腿要端正,不能架腿而坐,还特别说“眠不言,食不语”。
道理呢,白得很。吃饭掉粒米,浪费粮食,粒米百颗汗哟,菩萨看得见,响雷会打头的;从小就晃荡“二郎腿”,一副老相的样子不说,还可能引发不少病,这样的坐姿,绝对不合中华儒教的规矩。
“小娃娃懂什么啊”,奶奶溺爱地护着我们,母亲总是争着说:“没得规矩不成方圆,规矩要靠做,做的就是一种习惯;桑树只有从小撑绑,长大才能硬直。”严中温馨,似《论语》所曰:不学礼,无以立;应如儿歌《三字经》中所唱: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,苟不教,性乃迁。”
《礼记》:“共饭不泽手。”有“毋啮骨”之戒,所以“割不正不食”、“席不正不食”。中国人尊奉了几千年的雅训:玉不琢,不成器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:优秀是一种习惯。习惯不是天生的,是母亲用心“做”出来的,做人要有人相。
上小学时,有一天放学后,“田大眼”在我家赖皮,说是我“拿”了他借的小人书《地道战》。我是喜欢看小人书,可我没有“拿”他的书啊。他死说,那天是我负责打扫卫生的,而且是最后一个走的,真是有理说不清。
母亲回来了,问清缘由,看着急红了脸的我,又抚摸着“田大眼”可怜巴巴的头,从衣袋里掏出两张一角的钱,说:“一人一张,每人去买一本画画书吧。”
后来,“田大眼”在草垛洞口找到了《地道战》,我想去跟他要回一毛钱,母亲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多大的事啊,这已经过去了。”
那年高考,我落榜了,沮丧地躺倒在床。母亲却大大咧咧地劝慰我:“要学杨子荣,昂首挺胸!广播里不是常说:失意不能失志,消沉反会伤神,干吗非挤那独木桥呢?条条大路通罗马,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。”扬起眉毛,又说,“时间不说话,这都会过去。”
我当上了聘用乡干部,后来,又考上了国家干部,要办“农转非”,我回家拿农村户口簿,高兴地告诉母亲:“儿吃皇粮了!”
母亲头也没抬,淡淡地说:“要紧的是珍惜现在,这还会过去。”
偶然,读到这样一句至理名言:“这也会过去。”面对纷繁的世事,你要保持微笑,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、去面对,得意时不必骄矜,忘乎所以;失意时不必气馁,当奋发图强。
母亲淡淡的话,也涵盖着不凡的智慧。是啊,在无声的时间里,从从容容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个冬日和春天吧,在无声的时间里,因为“这也会过去”。
门前的小河,没日没夜地流淌着。清澈的水底,自由的鱼儿自在欢畅。
春天里,父亲劈开竹竿为竹条,编排成箔子,安插在小河中,再用粗壮的竹篙稳固好,簖,算做好了,就等着取鱼吧。
我们雀跃开了,屁颠屁颠地在河边吮指,那簖拦截整个小河道,任性的大鱼小鱼啊,看来插翅都难逃了!
母亲却要父亲把中间的竹箔锯断,要留个口门,也方便船行,父亲说,这条小河没有船行啊,母亲还是坚持说,锯吧,锯短些,簖对鱼杀伤力够大的了,要留下生门,放鱼虾们一点生路,积点德吧。
中国古代预测学玄学里有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的八门之说,生门为吉门。世上千事万物都是有磁性的,或弛或张,各行其道,做事都得有度,不可做绝,方能造化平衡,万事大吉。
以瓜菜代粮的年月,母亲变着花样改“膳”,常做胡萝卜饼子:先把面发好,再把煮熟的胡萝卜捣烂,和合之,就可以烙胡萝卜饼子了。
我们抢着去锅灶旁,这里不仅可以闻到饼香,还可以取暖。穰草推进锅塘,只是冒出青烟,刺眼呛鼻。母亲看看锅塘里堆得像小山丘似的穰草,“草把得慢慢添,火要抬着烧”。笑着说:“人要实心,火要空心。”
烙饼子,也很有技艺,冷锅底,面就会黏连,难成饼形;火太旺,铁锅火怒,饼子就会焦煳。母亲用很少的菜油抹下锅窝,待锅烧热了,才一一烙饼。
我们等不得了,脖子都伸长啦!
“锅不热,饼不靠啊。”母亲嗔怪道,“烙饼如同为人做事,要懂得分寸,要用心把住火候,心急吃不了热粥。”
母亲做胡萝卜饼子别出心裁,真是好看又好吃:有圆形的、有心形的,还有蝴蝶形的,让我们稚嫩的心灵长出灿烂的翅膀。我们一边吃着饼子,一边欢乐地唱着:“又甜又香,一直吃到栽秧,又香又甜,一直吃到过年……”
河对岸网小家的二丫头跟邻村东浒头的盛三小跑了!跑了,就是私奔,按辞书解释:“私奔”为“旧时指女子私自投奔所爱的人,或跟他一起逃走”。那年代,农村里家境不好的人家,常发生这样的事。
亲戚家全聚集在网小家,邻居们一家一人也被请来了,网小家人声鼎沸,像开了锅的饺子,亲戚们摩拳擦掌,邻居们义愤填膺:这还了得,小东浒欺负我大蔡堡!到盛家去,打东西!那时候,这种土方式流行。
母亲也去网小家了。嘈杂声中,母亲找到了木讷着的网小:“砸了,又得怎的?三大纪律还有八项注意呢。”
“你家养了三个小伙,站着说话不腰疼!”孩子姑妈对着母亲吼起来,“就是要去砸,谁叫他家拐骗了我家丫头!”
“我晓得!老盛家弟兄四个,两个光棍,就一个丁头舍子,家产可以说一担能挑走,能砸出什么名堂呢?”母亲面对众人说,“应该出气!可不能摸不到个喉咙就乱捅,三分帮忙真帮忙,七分帮忙帮倒忙。”
我父亲那时候当大队书记,母亲的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。噪声渐弱……
“大家都认得盛三小,小伙子还是挺灵猫的,就是家穷了点……雨下不到一天,人穷不到一世,草灰还会发烀呢!”母亲擦了擦眼角,说,“大家都看过电影《小二黑结婚》,二丫头又不傻又不呆,跑也许有跑的道理啊。”
这桩婚事后来还真是成了,而且非常美满:盛三到大城市里红红火火地开了装潢公司,二丫头现在回家开的是“小宝马”,网小一家住在家里享受二丫头带来的鸿福。